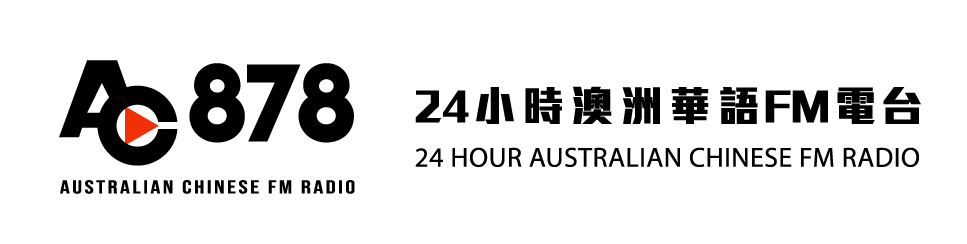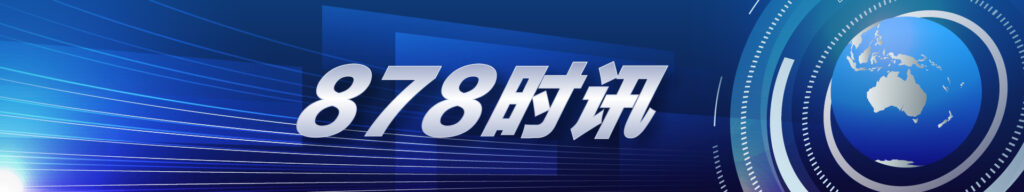工党暂时领先,但胜负仍然未知

随着联邦大选进入倒计时,工党止住了此前在民调中的颓势,并且将支持率重新提升至看似足以胜选的水平。
但现在还不是打开啤酒庆祝的时刻。所谓的“软性选民”——那些倾向某一方但仍可能改变立场的选民占比超过30%。这意味着仍有大量选民可能被说服,足以改变选举结果。
因此,达顿的团队尚未放弃,仍在积极寻求可能的“转折点”。
2019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当时的选举结果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。对工党来说,那仍是一道未愈的伤疤。
两届自由党内部纷争后,工党深信胜券在握,甚至拍下了那张自信十足、如今却显得格外讽刺的“我们准备好了”领导班子合照。
但在幕后,自由党阵营其实有自己的胜算。他们的内部民调通常不会公开,以免暴露战略——显示仍有一条胜利路径。
这条路径后来被称为“goat track(羊肠小道)”,Scott Morrison便是沿着这条狭窄的路径稳步前进,在民调指引下步步为营。
自由党的一位竞选老将称这场选战在技术层面上是“革命性的”。
与此同时,公众舆论也出现关键转折点。当时的财政部长候选人Chris Bowen在面对选民质疑政策时表示:“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政策,那就别投我们。”
这句话令部分选民果断转向。Morrison将那次胜选称为“奇迹”,但这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:“天助自助者”。
“转折点”在选战中向来至关重要,竞选团队一方面竭力制造“转折点”,另一方面又设法避免对手制造出这种局势。
自由党内许多当前的高级人物,仍对1993年John Hewson对阵Paul Keating的那场选战心有余悸。
当时John Hewson力图挑战Paul Keating,推出宏大的税改计划《Fightback!》。
其中包括后来的GST(商品和服务税),结果在一场电视直播采访中,Hewson在解释“生日蛋糕是否要加征GST”时结结巴巴,让选民印象大跌——这成了那次选举的决定性失误。
2001年选举的转折点则是精心设计的选题设置。
选战爆发于911袭击之后,国安议题成为焦点。John Howard以一句“我们决定谁能来澳洲、在何种情况下来”牢牢把握住了选民情绪,终结了对手Kim Beazley的上升势头。
2004年选举,工党领袖Mark Latham推出“Medicare Gold”政策,因缺乏资金来源而被自由党猛烈攻击。
更致命的是Latham与Howard的一次握手,被媒体捕捉到其气势汹汹的神情,进一步加深了他“性格冲动”的公众印象。
当然,工党也曾抓住自己的关键时刻。反对John Howard推出WorkChoices工业关系改革的宣传战虽非单一事件,但无疑动摇了自由党的执政基础。
而2016年的“Mediscare”行动,甚至在投票当天通过伪装成Medicare的短信轰炸选民,险些让Bill Shorten赢得胜利。
这场“恐吓式”选战也令联盟党提高了警觉,对接下来的2019年选举形成了警示,开启了融合“舆论转折点”与“民调引导策略”的新时代选战。
如今达顿正把希望寄托于类似的战术。他近日提出以“终结税级攀升”和能源政策作为长期繁荣的方向标。
国防议题也在其布局之中。他和团队正在努力制造一个有力议题,试图拓宽这条现代竞选中狭窄的“羊肠小道”。
是否奏效,还要等待选后才会揭晓。